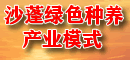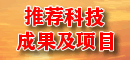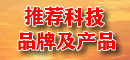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风险投资成长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心怀梦想的人是以怎样的雄心和毅力改变了高科技企业的成长环境,而这样的改变又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对于在20世纪中期已经长大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们一生当中都无法抹去的回忆。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境遇与常人略有不同:尽管二战后美国政府积极让几百万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但军方却非常急切地想留下多里奥特。如果考虑到多里奥特还是一个成年之后才来到美国的法国人,这一切就更加令人称奇。
1920年,21岁的多里奥特为躲避欧洲的战乱从法国来到美国。依靠父亲朋友写给哈佛校长劳伦斯-洛威尔(Lawrence Lowell)的介绍信,他得以入读哈佛商学院。在这里的最初几年,多里奥特就结交了美国后来的很多要员——虽然他们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这种态势在1925年哈佛商学院聘用他后更趋明显:他的学生往往可以在商界或政府获任要职。
多里奥特热爱祖国法国的一切,但也对“法国人化简为繁的杰出能力”深恶痛绝。他对创业企业及其带来的经济活力心向往之,对法国的政府管制式经济以及罗斯福新政中加税和反竞争的做法颇多异议。这使他在二战期间的美国军队中显得卓尔不群:在那个大型工业企业所向披靡的时代,他似乎比那些精英人士更懂得培育初创企业对提升经济活力的价值。
于是,二战结束后,多里奥特接到了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erson)的电话,后者希望由他负责战争部下属的一个专司研发的新部门。刚刚结束的战争充分证明了科技的价值,而多里奥特是为数不多持有这一观点的高级将领之一。为打消多里奥特的疑虑,战争部长帕特森又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自己也相信多里奥特是这个位子的合适人选。
与多里奥特一样,艾森豪威尔也意识到了科技对军队的意义。1946年4月30日,刚刚继任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就下发了一份极具远见的4页纸备忘录。在这封备忘录中,他列出了5点政策,以确保在新成立的研究开发部领导下,国家的各种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
“单靠武装部队无法赢得战争,只有加上科学家和商人提供的技术武器,我们才能获得胜利。”艾森豪威尔写道,“这种结合也要引入和平时期,这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军队了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还是为了借助国防计划把所有有助于保护国家的民间资源全部考虑进去。”
以官阶而论,等待多里奥特的着实是份好工作,但他却很快就心生厌倦,“战争期间随处可见的团队精神已荡然无存,大家没有做任何建设性工作,每个人都只靠军队养着。”多里奥特希望能在更务实的领域发挥力量,而机遇也就在这时垂青了这位理想远大的天才。
开启风投的大门
在逐渐散尽的硝烟中,时任MIT校长的康普顿(Karl Compton)终于得以抽身开始筹备一个在他心中谋划已久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创造一种为技术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资金的新型金融机构。当时,战争结束带来的军工和纺织产品的需求锐减,税负的加重和投资信托公司日益凸显的保守主义倾向,正使那些本应朝气蓬勃的新建企业遭遇严重的融资困境,这甚至已经在MIT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演变为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
康普顿认为就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技术的尽快商业化,而这又与金融支持密不可分。他和他的朋友们必须努力解决美国的低风险经济难题,从而使美国,当然主要是新英格兰地区不至对传统行业的必然衰败无能为力,也不至对新兴产业的缓慢成长作壁上观。
康普顿的思想反映了创新过程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关键因素——金融。创新并非旦夕之功,而是一个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漫长工程。没有资金支持,创新通常很难成功。类似的例子在过往的岁月中并不难以寻找,而其中最经典的例证无疑就是爱迪生(Thomas Edison)。
发明电灯的每周支出高达800美元,但爱迪生却无须为此担忧,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金融巨鳄,摩根对新兴产业的关注丝毫不逊色于他对推动产业重组的兴趣,他联合了另外两家财团共同支持爱迪生,条件是共同创办新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并由新公司持有专利权。
爱迪生因此同华尔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此以后,他在发明过程中再未遇到过资金问题——摩根运用金融手段帮助爱迪生不断把大脑中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而他本人也充分享受着发明创新带来的种种好处,爱迪生的第一台发电机就为摩根的办公室提供了照明用电。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整整13年后的1892年4月,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成为新的公司——通用电气。这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基业长青公司,其投资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从未落于下风,而这次合并的幕后推手同样也是摩根。
康普顿希望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摩根曾经扮演的角色。为此,他召集了自己曾经的部下: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分行行长弗兰德斯(Ralph Flanders)、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公司主席格里斯沃尔德(Merrill Griswold)和哈佛商学院院长大卫(Donald David)。康普顿希望,这些怀有梦想的社会名流能和自己一起共同建立一家针对风险行业的投资企业。
1946年6月6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成立,其创始人包括弗兰德斯、Taft-Pierce Manufacturing总裁布莱克索尔(Frederick Blacksall)、美国橡胶公司前董事杜威(Bradley Dewey)和MIT财务总管福特(Horace Ford)。
而作为一个兼有军方和新英格兰地区教育与工作背景,又对扶持新兴企业充满激情和愿景的人士,多里奥特毫无疑问成了新公司总裁的最佳人选。在公司的首份年报上,多里奥特非常正式地写到,“ARD的宗旨是帮助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成长为成熟而有价值的公司”。
在创办ARD的过程中,ARD的创始人们都很清楚企业的动态化特性。他们意识到掌握着庞大的信托资源的机构及其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发明创新并不在行,而发明家在研制创新产品时又缺乏资金的支持。ARD想把这两类相互联系、但很大程度上相互隔离的群体整合到一起,公司的创始人们决定出售20万份公司普通股筹集500万美元的公司资本。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ARD并非美国战后成立的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1946年初,两个富有的东海岸家族就已经先于ARD建立了其各自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就是同样著名的惠特尼公司(J.H. Whitney &Company)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Rockefeller Brothers Company)。
但ARD是美国第一个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他的资金并不依赖于富有的个人,而是源于保险公司、教育机构和投资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这极大地扩展了有助于增加风险资本总额的潜在资金额。同时,ARD还与众不同地寻求使企业管理变得更加专业和透明,并愿意为此向新建立的小企业提供管理支持,而随后的历史证明这比单纯的资金支持更加重要。
点燃创业的激情
人类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习惯性地低估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头脑中的美好要转换成现实中的强大,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强大而真诚的意愿,有时候还要依靠丰厚的物质奖励去赢得社会的认同,而后者往往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对于ARD的起步与发展,问题同样如此。
截至1946年底,ARD只卖出了总计20万股中的13万股,350万美元的总筹资额中有180万美元来自9家金融机构、2家保险公司和4家综合性大学,其余的资金都来自于单笔投资不得少于5000美元的个人投资者。这对于这些心怀梦想的人来说,不啻于一个巨大的打击。
当银行和董事们还在为筹钱焦头烂额的时候,ARD的运转已经开到了最大马力。蜂拥而入的上千家公司已经让这里无法再享受闲适的生活,对变革的向往让这些人不再畏惧前途略显渺茫的生活。弗兰德斯不断强调ARD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场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很多人常常问我仅凭这几个人怎么开展工作,
我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团队其实是整个美国”。
社会的巨变也在呼应这种全新的资本运营模式,战争这时成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分水岭。
战争鼓励冒险,商业竞争则证明这种精神的价值远超想象;战争改变了资本市场,战时开发的新技术让很多投资者更愿意冒险去支持这些项目的发展;战争改变了市场,盟军的胜利和凋落的欧洲意味着美国企业必将突破北美;战争还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加速形成,《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几百万人走进大学,培养技术专家和企业家成了全社会的诉求。
战争也促使政府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1938年,纯理论科学的研究经费还不足4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行业资助。但到了1943年,仅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就与大学签订了90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基础研究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新的商业机会即将迎来井喷。
从一开始,ARD就设置了非常高的准入门槛。他们拒绝了在极地冰层下开采石油的商业计划,拒绝了在机场修建脚踏车跑道的建议,也拒绝了用热水肥皂沫代替厕纸的想法。他们只关注新兴产业以及在新兴产业中拥有核心技术的代表性公司,在任何一个财政年度,ARD投资的商业计划比例都不会超过总申请数量的4%,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只占总量的1%~2%。
1946年底,在做了大量工作后,ARD终于选定了第一批的3家新兴公司:生产气化润滑油注入装置的Circo Products获得了15万美元;生产高压发生器的高压工程公司获得了20万美元;还有15万美元投给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是历史上第一个涉足原子学领域的商业企业,但当时,这家因出售放射性同位素和制造放射性探查设备而闻名的企业已经濒临破产边缘。
第一轮投资反映出ARD的投资理念已经超越了“货币投资”的阶段,上升到了包含必要时提供管理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的境界。多里奥特进入了高压工程公司的董事会,康普顿加入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多里奥特的助手罗伯特·霍农(Robert Hornung)则成为了Circo Products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在1949年年报中,多里奥特对这一做法解释道,“无畏而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与明智且经验丰富的长者组成的管理团队一定能获得成功”。
不过直到那一年年底,除了花钱如流水,ARD还没有做过一件被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公司41%的已支付资金全部投资在缺乏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上,这意味着公司没办法获得短期回报。而在已经投资的8家公司中,只有两家实现了盈利。多里奥特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ARD失败了或者是业绩不好,那么这种实验性的风险投资操作都很有可能会从此销声匿迹。
持续的亏损和紧张的筹资造成的糟糕财务状况,几乎贯穿了ARD最初几年的经营活动。“当公司组建时,有人就曾说过只要10个项目中有一两个项目成功,那么ARD就做得不错了。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实际业绩明显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1948年底,在给股东的信中,多里奥特写到,“公司能够在明年实现盈利,ARD将成为向有潜质的美国企业提供资本支持的重要因素。”但那一年,ARD又亏损了44000美元,公司资本已经减少到了120万美元。
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成功无疑太重要了。1948年,该公司收入翻番并获得了37000美元的利润。于是,ARD宣布他获得了第一笔37000美元的资本利得:他以每股29.93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其持有的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1765股股票。
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威廉·巴布尔(William Barbour)对多里奥特极尽溢美之词。他称后者在关键时刻将他从日常琐事的纠缠中拯救出来,从而把握住了企业最佳的成长机遇。这让多里奥特信心大增,而改变历史的机遇也终于在坚持中逐渐到来。
DEC:风险投资的催化剂
当奥尔森(Kenneth Olsen)和他的同窗好友安德森(Harlan Anderson)拿着一份4页纸的商业计划书,站在ARD的评审团面前并告诉后者他们将制造出比IBM更便宜的计算机时,改变风险投资历史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只不过,当时身在局中的大家都对此茫然而不自知。
多里奥特认为奥尔森是“一位少见的一流素质的人”,这使他下定决心支持奥尔森当时尚算粗糙的创意。多年之后,多里奥特当时所信奉的这条原则成为风险投资领域共同的圣经,“可以考虑对有二流想法的一流企业家投资,但不能考虑对有一流想法的二流企业家投资。”
奥尔森所要求的投资只有10万美元,但他们计划进军的计算机领域却令ARD难下决心。当时,这个价值25亿美元的计算机市场已经被IBM等企业瓜分殆尽,很多红极一时的美国企业都在涉足计算机市场时损失惨重,ARD不相信区区10万美元就能动摇现有的行业格局。
为了掌控公司以规避风险,ARD最终以7万美元换得新公司77%的股份。同样是按照ARD的要求,新公司被最终命名为数字设备公司(DEC)。ARD不希望新公司因名称中包含“计算机”之类的字眼而激怒强大的IBM公司,因为这会令新生的公司尚未成功就胎死腹中。
ARD还严令奥尔森必须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因为在ARD的董事会中,弗兰达斯和福特等重量级的董事都年事已高,他们可能不愿意在有限的生命中继续投资一些不能在短期内实现盈利的企业了。奥尔森马上就就答应了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没关系,我们可以保证第一年就实现盈利,我们还能保证我们新公司的利润率一定会高过那些著名的计算机公司。”
这种为寥寥数万美元出卖公司控制权的做法在今天看来颇不明智,但奥尔森和安德森却对这一协议全无异议。“他们不知道别的公司如何分配股份,但他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接受ARD公司提出的分成法和7万美元,要么连同投资款、创意和公司都放弃。”
事实上,奥尔森毫不在意这份协议条款的严格:“7万元的好处是你必须锱铢必较地勤俭创业。”同时,尽管多里奥特直到1972年才最终进入DEC公司董事会,但他从一开始就是奥尔森最坚定的支持者,并对公司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都令年轻的奥尔森受益匪浅。
在那之后的9年时间中,DEC公司再未进行任何股权融资,直到公司上市,因为ARD的支持不仅包括股权融资。1958年,ARD为DEC提供了一笔3万美元的贷款;1963年,当DEC公司需要更多资金以发展自己的计算机业务时,ARD为他提供了一笔30万美元的贷款。
员工高涨的热情更是极大地弥补了资金短缺的瓶颈。创建的第一年,DEC公司就推出了第一批产品——数据实验室和数据系统组件,为公司带来了139.4万美元的收入和少量的盈利。在当时的新建企业中,这一少见的佳绩意味着DEC公司可以开始实现其计算机梦想。
1960年底,DEC公司的第一台计算机——程控数据处理机(简称PDP-1)上市了。PDP-1把通用计算方法带给了新的用户阶层。他的体积只有冰箱那么大,他和显示屏一起组装在一个落地框架里,这在当时的计算机行业中是前所未有的。尽管PDP-1只有4K的内存,每秒钟只能进行10万次加法运算,但其12万美元的价格足以抵消所有的不足——他太便宜了。
成功很快转化为吸引优秀人才的巨大魔力。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MIT那些杰出的师生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1960年6月,贝尔(Chester Bell)来到DEC。在这里,他成为仅次于奥尔森的二号人物,正是他创造的计算方法使DEC公司成为IBM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965年,DEC公司推出了PDP-8计算机,其定价竟然只有18000美元,这一价格远远低于其他公司任何同类产品的价格,PDP-8立刻成为市场热门。随后15年中,DEC公司卖出了5万多台PDP-8,这使得DEC的收入在随后20年中始终呈现出几何增长的强劲势头。
没人知道这家公司的极限在哪里。1986年10月,《财富》杂志把奥尔森评为美国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其排名甚至在汽车大王福特之前,这一切依稀如同今日之乔布斯。这时,DEC公司的销售收入达到130亿美元,其纯利达到了惊人的11亿美元。这时的DEC公司拥有雇员112万人,并在《财富》500强榜单上杀入了前30,他已经是马萨诸塞州最大的雇主。
作为资本大戏的最高潮,1966年8月16日,DEC公司成功上市。奥尔森突然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当初放弃的控制权为他带来了5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尽管他仍然坚持穿着那套皱巴巴的衣服,但他也承认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巨变,“我现在可以再买一把独脚椅了”。
比奥尔森更高兴的当然是ARD。这一天,ARD公司的账户中增加了3850万美元。这意味着在过去的9年中,ARD的投资年均资本回报率高达100%。而在巅峰期,最初的7万美元总计为ARD带来了高达3.7亿美元的收入,这一数字已经相当于当初投资额的5000倍。
在20余年的岁月中,多里奥特曾先后帮助那些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创建过150家公司,其中成功上市的也不在少数。但其中再没有任何公司取得堪比DEC的辉煌。如果从公司成立之日算起,ARD的年均综合回报率约为14.7%;但如果没有DEC,这一数字仅为7.4%。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投资回报非常规的高企,通常都是资本游走的惟一动力所在。于是,作为风险投资历史上最伟大的产业催化剂,ARD在DEC上收获的巨大资本回报标志着一个属于勇敢者——风险投资家的时代至此终于正式到来了。
护花春泥的荣与衰
从某种意义上说,ARD的成功率先成就的却是作为新英格兰地区竞争对手的硅谷地区。
从DEC的成功和ARD创造的财富神话开始,硅谷高科技企业中迅速兴起了一类新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而其代表无疑就是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和曾为“八叛逆”之一的尤金-克莱纳。前者同时还是举世闻名的硅谷四大风险投资家之一,另外3个分别是阿瑟-洛克(Arthur Rock)、约翰-杜尔(John Doerr)和维诺德-科斯拉(VinodKhosla)。
这些企业家在成功创业后,又把他们积累的资本连同那些更为重要的制造工艺、运作经验和产业联系网,重新投入到那些有前景的企业中。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大量参与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他们提供商业计划建议,帮助企业寻找合资者,招募管理者,当然也直接出任董事。
政府政策的调整也在这时促进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宣布将风险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从49.5%减少到了20%。养老基金等社会资本因此更容易投资到风险资本合伙企业中去。也是从那时开始,美国社会资金向风险资本的流动有了明显的加速。
以占经济总产出的份额来衡量,美国风险资本产业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风险资本产业也经历过迅速的增长。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增长更加迅速,这意味着他实际上拉大了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
与人们想象的情况高度一致的是,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的投资相当集中。从1965年到1992年,四大产业——办公和计算机、通信和电子、制药和科学仪器——共同占据了所有美国风险资本产业投资的81%。到上世纪90年代,因特网相关投资又占到风险资本投资总额的70%以上。而所有这些部门,恰恰构成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赢得与全球比较优势的关键。
但就在产业逐渐繁荣的时候,ARD却出人意料地日渐凋零,直至最终成为护花的春泥。
在编写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时,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的是想借助该法案禁止投资公司通过投资控股方式把触角伸得太长,而投资控股恰好是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公司惯用的手法。于是,法案规定一家投资公司不能持有另一家投资公司超过3%以上的普通股。有了这项规定,马萨诸塞州投资信托公司就无法大量买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的股票。
幸运的是,ARD的创始人们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人脉关系,这为他们争取到了很多政策特权,其理由是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这些豁免权包括允许ARD持有其他公司5%以上的股权,允许其他投资公司购买ARD不超过9.9%的股权,允许ARD向投资公司出售股票。最后,基于ARD已经收到了300万美元的股票认购款,ARD的股票发行计划也最终获得批准。
但政策的制约至此并未被梳理完毕,更大的问题一直在等待着多里奥特和他的支持者。
从1959年开始,多里奥特的公司开始面临一种新的局面,那就是新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采用一种诞生于德州石油勘探工业的有限合伙制。这种形式不但可以要求合伙人不参与管理,还可以使那些基金管理者在获得常规管理费的同时,再以免税的形式获得部分投资盈利。
不过,所有这些好处,作为上市投资公司ARD的高管们无缘分享:按照法律要求,他们不能购买那些受资助公司的股票期权。资金供求双方的境遇因此经常呈现出强烈的对比:那些受资助企业的创立者们经常因为公司上市而身价倍增,ARD的高管们却只能要求最多2000美元的加薪。多里奥特为此多次向美国国会和证监会上诉,但每每无功而返。
作为ARD公司总裁,多里奥特从来不急功近利也不甚计较私利。他结婚48年,膝下无子,因此他专注于培养手下并将他们视若己出。他说:“当你有了孩子时,你不要期望他给你什么报答。当然,你可以希望孩子将来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对你最好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善良忠诚的人没有做出作为报答的成绩,我也还是会看重他的。”
上世纪60年代晚期,年事已高的多里奥特在寻找继承人时,相中了他以前的学生汤姆斯-佩金(Thomas Perkins),佩金当时领导惠普的研究部门颇有建树。令多里奥特失望的是,佩金找了一个礼貌的借口婉拒了他的盛情邀请,显然,佩金隐藏了自己的实际动机:他拒绝多里奥特,其实是因为ARD的结构决定了作为其领导者的总裁不可能赚到大钱。
此后事情的进展不出预料。1972年,佩金在参与建立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时把他建成了有限合伙人公司。之后不久,多里奥特终于认清证监会不会就股权问题做出任何让步。于是,他无奈地宣布ARD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尽管他当时依然持有超过120家高科技公司的股票。又过了不久,年事已高的多里奥特将ARD并入了飞行器托拉斯公司Textron并在之后宣布正式退休。
历史令人唏嘘不已。但同样对于这段历史,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大卫-休(David Hsu)有着自己的解读。他告诉那些ARD的缅怀者,虽然ARD因为结构的致命缺陷而无法良好运行,但他在风险投资行业留下了长足的影响。到多里奥特把ARD卖给Textron时,“风险投资已经成为经济的一部分,ARD只是在其历史使命完成后退出了舞台。”而对于多里奥特这位曾以解决美国的低风险经济难题为己任的开拓者来说,这足以名垂青史。
责任编辑:梁宏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自其它媒体的文章,目的在于弘扬科技创新精神,传递更多科技创新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在此我们谨向原作者和原媒体致以崇高敬意。如果您认为本站文章侵犯了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