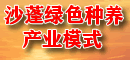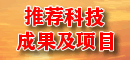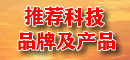若不及时实现油气产区、领域的战略性接替,推动探明可采储量明显提高,将导致我国未来近中期可能出现先石油、后天然气不能稳产甚至较快下降的风险。根据碳达峰、碳中和指标约束下能源需求及其构成的预测成果显示,今后30-40年仍将有相当数量的油气需求,其中天然气将在能源转型中发挥过渡和桥梁作用,是非化石能源的最佳伙伴。因此,需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持续对新区、新领域实施第三次油气勘探战略,保障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需要油气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主流社会的共识,世界和我国能源结构将在未来30-40年内出现颠覆性变化,从以化石能源为主体变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因此,要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的同时,逐步缩减化石能源消费的份额和数量。因此,一些观点提出了“绿色金融”的概念,不仅提出大幅缩减对化石能源的投资,还要求金融机构不再贷款,导致煤炭、石油是“夕阳产业”等论调出现。但需要注意的是,能源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
实现《巴黎协定》的路径主要有两条:节能增效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满足人类发展需求;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变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即能源转型。
我国能源转型的路径必须立足国情、符合国情,从能源结构的现实情况出发探究。受生产力发展程度制约,能源结构从柴薪时代进入化石能源时代,再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非化石能源时代,其中化石能源时代又分为煤炭时期、石油时期、天然气时期。有数据显示,2020年,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占比分别为56.5%、19.6%、8.2%,水电、核电和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占比分别为8.1%、2.2%、5.4%,表明我国处在化石能源时代的煤炭时期。相比之下,西北欧一些发达国家已进入天然气时期。一般来说,时期和时代的更替只能加速而难以跨越。
在能源转型中,化石能源将从主要作为能源燃料变为主要作为碳基化工原材料,生产出种类更多、价值更高且目前多需大量进口的高端产品;在油气下游,从目前的炼油、化工“二八开”变为“八二开”;煤化工、油气化工的占比情况取决于节能环保、降本增效的实际效果。
化石能源承担为非化石能源调峰补缺的重任。作为非化石能源主力的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受气候影响明显,且难以准确预测,从而形成不规则的峰谷差,再叠加其他负面因素时易造成影响较大的供应危机。而且,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大时,为保障安全稳定供应所需的调峰补缺等辅助服务呈指数级增大。其中,气电、油电有较大的灵活性,但价格较高,并已承担较重的保供压力;煤电价格较低,但启动、关停不够灵话。无论由谁承担调峰补缺的重任,付出的经济代价都应由非化石能源承担并计入经济运行成本。
可供经济开发的石油“入不敷出”
全球流行的油气储量-产量年报中首先被列出的是各国家/公司的剩余经济可采储量并统称为储量,被看作是实际存在的资产,也是评估今后油气储量和产量走势的较可靠依据。我国油气上游以储量、产量为核心的一系列基本数据反映在每年的《全国油气矿产储量通报》(下称《储量通报》)中,其基础是地质储量,即允许有30%误差的探明地下油气蕴藏量,并以其为基本参数对社会公布。同时,在供内部使用的报表中,以标定或预测的采收率×探明地质储量得到可采储量。
分析《储量通报》相关数据可以发现,近10年来,我国石油勘探年新增石油地质储量相当大,年均值大于 10×108吨,其中2012 年为15.22×108吨。由于这是对外公布石油勘探业绩时的首要(往往是唯一)数字,可能使业外人士对勘探形势产生误解,即“近年来的石油储量持续高位增长”,却并未关注其中存在的问题。
其实,近10年我国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和经济可采储量均呈总体变小的趋势。如新增原油探明地质储量前5年年均增储12.12×108吨,最大值为2012年的15.22×108吨;后5年年均增储10.28×108吨,最大值为2020年的13.0×108吨,主要原因是勘探难度增大,反映了勘探投入不足和国际油价变化的影响。
同时,根据《储量通报》给出的原油累计技术可采储量计算采收率(即与地质储量的百分比),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28.6%和28.5%,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 26.4%和26.1%(2019年的经济可采储量为前两年的采收率得出的推算值)。笔者根据新增石油探明经济可采储量计算采收率,2010年和2011年皆为16.5%,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13.5%和14.1%,2020年为13.0%。这两组数据均反映了新增石油储量劣质化。
总体来说,近年来新增石油探明经济可采储量与该年产量的比值(储量补充系数)整体小于1,仅2011年和2012年略大于1。石油剩余经济可采储量呈减少趋势,2016-2018年,新增石油经济可采储量均值为1.30×108吨,平均产量为1.79×108吨,储量替换率仅为0.73。2019、2020年新增经济可采储量分别为1.3×108吨、1.69×108吨,原油产量分别为1.89×108吨、1.8×108吨;2019、2020 年储量补充系数分别为0.65、0.89。若考虑到年新增石油经济可采储量实际上有所夸大,那么储量补充系数小于1的情况将更加突出。
形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过长期勘探开发的老油气区新增有经济效益储量的难度增大,可供经济开发的石油“入不敷出”。因此,亟需新区、新领域的战略接替,获得更多明显的经济效益储量,保障石油产量稳定或增加。
石油经济可采储量有限
石油产业链最上游是勘探。在经历漫长曲折的探寻并投入不菲的资金探明油气田后,持有者往往要尽快开发,获得收益以偿还/补偿前期大量的勘探投入,并获得继续发展的资金。一般情况下,持有者会迅速建设产能、完善外输设施,用不长的时间开发全部已探明储量,力求尽快提高产量。只有在油气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特别是供大于需且新开发油气的市场价难以与已开发的油气田竞争时,才会将批量探明储量长期搁置、不予动用。中东和俄罗斯许多大油气田就出现过类似情况。
相比之下,我国相当数量石油探明储量长期未开发(动用)的情况特殊,至少从21世纪初就显示出原油累计未开发储量及其占比增高的趋势。2010-2018 年,原油累计未开发地质储量由73.6亿吨增至92.9亿吨,增长62.2%,占比由23.7%增至24.4%;原油经济可采储量的未开发储量由8.4增至11.9亿吨,增长42.7%,占比由10.9%增至11.9%。2020年经济可采储量的未开发储量达12.9亿吨,占比增至13.2%。
我国石油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产量不足、长期需要进口,目前石油进口依存度增至 74%。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保障能源安全的问题再次摆在我国面前。对此,我国持续进行已探明油气储量的开发和未开发储量的有效动用。在这种情况下,储量表上却仍有未开发的近百亿吨地质储量、10余亿吨经济可采储量,且近10年油气未开发储量占各自储量的比例呈增势,唯一能说得通的原因是,相当数量的“经济可采储量”实际上不能实现有经济效益的开采。这种实际不可采的储量既表现在长期存在的未开发储量中,也多隐藏在剩余的经济可采储量中。笔者根据储量表上的数据计算了10余年来石油未开发经济可采储量占全部经济可采储量的比例为10-12%。
回顾历史,上述情况主要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勘探与开发的条块分割。勘探强调认识地下的油气赋存,并以探明的地质储量作为业绩奖惩的标准。即使评价储量的经济性,对成本和价格等关键参数的估算也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导致油气经济可采储量失真。随着能源加快转型,国际石油产量峰值过后,总需求量将明显趋低,将使得国际油价趋低,进而提高石油经济可采的门槛。
在油气系统报表中,储产比指剩余可采储量与当年产量的比值,即在二者都不变的情况下研究油气在理论上还能开采多少年。根据《储量通报》计算石油储产比,2010年为12.1,2018年为14.5,笔者推算2019年为13.3。当按要求将未开发的剩余经济可采储量减计时,储产比将大幅降低,笔者以此方法计算,2010年的储产比为7.70,2018年为7.73。因此,许多研究者在讨论储产比时,将按《储量通报》计算的值称为“表观储产比”,以示与真实储产比的区别。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临界储产比”概念,表示当储产比低于某阈值时,该国家/油气区生产可能出现快速递减转折。在条件较好的国家/油气区,“临界储产比”可选10;在油气投资和设备难于到位及油气勘探条件困难的国家/油气区可选15,目前我国属于前一种情况。
天然气储量产量增长趋于平缓
根据我国相关规范,常规天然气包括气层气和溶解气。溶解气的赋存和产出与原油有关且在天然气总产量中占比较低(2019 年占天然气产量的 6.3%),在油田开发初期常因利用条件不充分导致部分溶解气被放空烧掉。因此,笔者仅以气层气为对象讨论天然气的形势变化。
近年来,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处于缓慢上升中。2010-2018年,新增天然气探明经济可采储量年均增长率为 5.3%,虽与21 世纪初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相比明显减慢,但与石油开始下降相比具有趋势性差异。根据《储量通报》气层气累计技术可采储量计算采收率,21世纪初多在60%以上,此后降至60%以下,如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58.2%和57.5%,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46.0%和47.5%,主要由新增天然气储量的品质变差所致。总体来看,新增天然气储量质量处于中等水平。
近年来,新增气层气探明经济可采储量明显大于年产量,即储量补充系数大于1,如2010年、2015 年、2018年、2020年分别为2.43、1.67、2.22、2.49。一般情况下,天然气储量补充系数高于石油,这与其开发相对滞后有关。天然气开发要求有完备的产能建设、管输、储库和下游使用系统。这使得2020 年天然气剩余可采经济储量达2010年的1.64倍。
与储量变化相呼应的,是近年来天然气产量增长有变缓趋势。2010-2013年,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率为 7.3%;2014-2020年,年均增长率为4.9%。由此可见,天然气仍处在储量产量增长曲线平台期前半部,但增长势头趋于平缓。
同时,近年来,气层气各类未开发储量占比略有增加。其中,2010-2018年,未开发经济可采储量占比为10.9-12.7%,总体呈渐增趋势;2020年达34.5%,未来近中期仍将延续这一趋势。2010-2014年4年间气层气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2.4%;由于2015年和2016年气层气产量下降,2014-2019年5年间年均增长率仅为3.8%,气层气产量由快速上升转入平缓增长。近年来气层气储产比约30。
无论从产量变化趋势还是储产比来看,气层气均处于增长阶段,尚未转入下降拐点。
页岩气增长突出但后劲不足
页岩气勘探开发被列入独立矿种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快。《储量通报》在2014年首次列出页岩气储量,其经济可采储量为135×108立方米,当年产量仅为11×108立方米。2018年的经济可采储量为1313×108立方米,当年产量为109×108立方米。4年间经济可采储量年均增长率为76.6%,产量年均增长率达77.8%。2020年页岩气产量达200.55×108立方米(占全部天然气年产量的10.7%)。显然,页岩气起步良好,储量产量均快速增长,在全部天然气增长中占据相当大比例。但同时,需注意页岩气的生产特点:
页岩气产量变化曲线呈 L 形。单井投产最初3、4年高产后快速下降,再转为长期低产并平缓下降,即使后期采取增产措施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特点。
页岩气生产采用多平台丛式井密集排列的工厂式开发,可较快完成全部可采储量面积覆盖。此后,虽可通过二次压裂等技术提高采收率,但产量仍将明显下降。截至2020年,页岩气大规模开发仅5年,但开发面积达40%,而已开发50年余年的气层气开发面积为65%,可见其开发程度较高。目前页岩气储量、产量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东南部埋深小于4000m的五峰-龙马溪组底部。如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使页岩气产区在平面上、埋深上、层系上有所拓展,待现有产区的初期高产期过后,产量将大幅递减,将致使页岩气难以获得持续发展。
需重新评价煤层气的资源潜力
我国煤层气被列为独立矿种开发较早。由于我国煤炭储产量高,因此曾对煤层气远景寄予厚望。广义地说,煤层气产量包括从地面钻井达到煤层开发的气量和从煤矿矿井巷道中抽采的气量(瓦斯)。但各地在后者开采和利用的统计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别,难以统一计量,特别是其利用率低,因此尚未被计入《储量通报》。近年来,煤层气有以下情况值得关注:
新增地质储量变化大。2001-2008年,储量增长几乎停滞;2009-2010年快速增加,2010年突增至1115×108m3 ;2011年后急剧下降,2019年新增地质储量仅为64×108m3。年新增煤层气经济可采储量呈同样趋势。造成对中起伏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体制变化和投资不足。
煤层气未开发储量占比高。2010年占比达99.4%,2018-2020年达80%左右。开发实践表明,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储量计算标准不符实际、储量审批标准过宽。
近年来煤层气产量增速明显下降。根据《储量通报》相关数据计算,2010-2015年,煤层气产量年均增长率为38.9%。这使得煤层气产量连续3个五年计划没有达到预定指标,2019年煤层气产量仅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2.3%。
目前煤层气储量、产量的类型构成与资源量研究成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根据资源量计算,我国高、中、低煤阶的煤层气占比基本“三分”,其中高煤阶煤层气占总量的29.7%,目前已探明储量的96%、产量的88%集中在高煤阶;资源量中埋深 1000m以下的煤层气占比为38.5%,我国煤层气储量的97%、产量的94%集中在该区域。这说明我国煤层气资源量估算存在较大问题,应重新评价我国煤层气的资源潜力。
尽管我国许多盆地、地区都进行了煤层气普查和勘探,但目前在国家补贴下可以进行经济开发的地区仅集中在沁水盆地中南部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区的煤层气产量分别为64.8%和31.0%。因此,要实现煤层气快速持续发展,需强化基础研究和完善系列技术,在管理上打通煤系致密气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界限。
如前所述,我国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发展均处于上升期,但不同程度存在发展速度趋缓和可持续发展前景不明确的问题,需认真对待。
我国的油气供需形势表明,石油的经济可采储量和产量难以保障其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同时天然气上升趋缓,这与近中期能源转型的实际需求存在矛盾。而且,我国在相当低的石油、天然气占比情况下仍有较高的进口依存度。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4%、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3%,且近中期仍将上升。
我国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把油桶提在自己手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且不说近中期大幅、甚至完全实现“电代油”“氢代油”的经济可行性,仅不断增长的油气进口依存度就是明显短板。因此,针对我国的国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要求近中期仍需加强油气勘探开发,不仅要在老油气田继续提高采收率、开发未动用储量,更要及时完成油气新区、新领域的新一轮勘探战略,进而实现油气产量持续增长。
(张抗曾任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张立勤系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自其它媒体的文章,目的在于弘扬科技创新精神,传递更多科技创新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在此我们谨向原作者和原媒体致以敬意。如果您认为本站文章侵犯了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