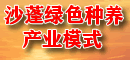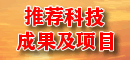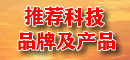小小

在南非一个洞穴深处发现的神秘尸骸正挑战着人们长久以来的信念,即双足猿如何进化成我们称之为“人类”、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生物。这些化石是在2013年发现的,很快就被认为是新物种的遗骸,此前从未见过。它被命名为“纳勒迪智人”(Homo naledi),这个物种出人意料地混合了现代人特征和原始人的特征,包括相当小的大脑。不过,纳勒迪智人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不是遗骸本身,而是他们的“安息之地”。
发现化石的那间石室离洞口很远,只能通过一段狭窄而艰难的通道进入,并且完全笼罩在黑暗中。科学家们认为,这个石室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接近,需要垂直爬升一段旅程,并需要通过只有20厘米宽的空间,身体受到挤压。这里不可能是用于生活的场所,对大部分人而言,充作临时落脚地都不大可能。这些细节促使研究团队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假设:尽管“纳勒迪智人”只有很小的大脑,但他们已经有了将“遗体葬在墓地”的萌芽想法。他们总结道,这个洞穴是一个墓地。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殓葬仪式对于追踪人类独特性出现的时间非常重要,尤其是象征性思考(Symbolic thought)的能力。象征性思考使我们能够超越现在,铭记过去,并展望未来。它让我们能够想象、创造并改变我们的环境,而这些都对地球产生重大影响。使用语言是这种精神抽象能力的典型体现,但研究它的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语言不是化石,无法留下物理记录,但殓葬可提供帮助。
殓葬可给出古人类行为方式的物质记录,而这些行为在精神上有重要意义。此外,殓葬还能帮助科学家追踪似乎是人类特有的信仰、价值观和其他复杂想法的起源。现代智人无疑与现存在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然而,准确地指出我们与大自然中其他物种的区别依然是非常困难的。
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毫无疑问,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其进化历程也与其他生命相伴。人类学家已经缩小了人类独有特征的范畴——抽象思维能力。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能够想象和交流眼前事物的能力是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这与简单、原始的沟通迥然不同,后者多与附近是否有食物或危险迫近有关。
人类使用符号来交流和传达这些抽象想法,我们还赋予非实用的事物以重要意义。例如,艺术和珠宝传达了关于信仰、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概念。殓葬仪式也被视为是象征性思维的典范,为死者精心料理后事的做法,其实蕴含着一整套复杂的观念体系。悼念死者有着铭记过去的意义,同时也展望我们终有一死的未来。这种抽象极为复杂,看起来惟有我们人类才有如此思考问题的能力。
这种理论背后假设,殓葬仪式只出现在现代人身上,或是他们最亲密的近亲中。那么脑容量很小、生活方式极为原始的纳勒迪智人也对尸体进行蓄意处置,这不仅仅是对这些行为起源的时间线提出挑战,它还颠覆了传统观念,即现代人类与早期物种之间的区别,甚至扩展到我们与自然的区别。
对于人类来说,死亡是个非常有文化意义的过程。世界各地的文化都以各种仪式来纪念死者,这些仪式传达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抽象的思想。自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已经研究了这些殓葬行为,以了解其他文化的宗教和信仰。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其他的生物,甚至其他的古人类,包括猿类属的灵长类动物以及南方古猿以及其他近亲物种也可能会有类似的行为。当然,人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在这样一个抽象的世界里,只有人类才会赋予死亡以深刻的意义。
然而,这种行为肯定是在我们进化史上的某个时刻出现的。由于在考古记录中,像歌曲和舞蹈这样的习俗仪式是看不见的,科学家们遂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殓葬这样的物质方面,以追溯殓葬仪式的历史。这些发现很快就引发了关于传统观点的尖锐问题,因为这表明,殓葬仪式可能并不是现代智人所独有的。
第一次关于“非人类埋葬死者”的辩论发生在1908年,当时在法国La Chapelle-aux-Saints附近发现了一具相当完整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骨架。发现者认为,这具骨骼显然是被精心埋葬的。对他们来说,坟墓被挖掘成类似乳房的形状,死者身体被摆成胎儿的姿势,而且被严密包裹起来。许多当代科学家仍然对这种解释持怀疑态度,或者直接否定了这些证据。后来的怀疑论者认为,20世纪早期的挖掘技术过于草率,无法得出如此完整的结论。关于La Chappelle尼安德特人埋葬之所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尼安德特人中出现殓葬行为,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惊讶。自从1856年在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山谷首次发现尼安德特人化石后,这个物种就始终与人类存在着“暧昧”关系。尼安德特人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之一,他们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光谱上的位置始终存在争议。在被发现后的100年里,他们通常被认为是高度非人类生物,他们的原始方面显示,他们可被称为“甚至不能站直的野蛮人”。
最近,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改观。有些科学家认为,这种生物与人类如此接近,以至于在地铁上穿上西装和戴上帽子后,尼安德特人甚至不会受到太多关注。关于尼安德特人墓葬的争论同样摇摆不定。在某些时候,科学家们相互指责对方过分“人性化”我们的近亲物种,而在其他时候则是对它们过于强调“非人化”。
1960年,在伊拉克沙尼达尔(Shanidar)洞穴的发现表明,光靠推断确定尼安德特人行为以及试图从粗略的残骸中了解他们的认知过程很不可靠。在沙尼达尔研究化石的挖掘人员发现了许多尼安德特人举行殓葬的证据。其中一处墓葬似乎特别有趣:围绕被称为Shanidar IV个体周围的土壤样本显示出花粉成分。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拉尔夫·索莱茨基(Ralph Solecki)认为,这些花粉就是殓葬仪式的证据,在尼安德特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五颜六色的花朵被放在坟墓里,这与现代人的葬礼方式十分相似。
在索莱茨基看来,这种“花葬”表明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这是首次在人类边缘物种中发现这种情感。他认为,科学家们不能再否认尼安德特人拥有“全部的人类情感”。但是,当围绕着Shanidar IV的花粉被发现是穴居啮齿动物带进来的时候,索莱茨基的理论崩溃了,因为这些啮齿动物用独特的方式扰乱了土壤成分。花葬假说的失败使科学家们在基于有限的化石证据断言人类信念时变得更加谨慎,那或许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非事实真相。
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尼安德特人确实埋葬了他们的尸体,至少有些尼安德特人确实那样做了。更麻烦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尼安德特人是否以类似于现代人类的方式思考死亡,思考诸如来世之类的抽象思维?或者埋葬是否是在通过处理腐烂的尸体让生活空间变得更舒适?
人类学家一致认为,即便按最乐观的估计,现有证据也难以确切地证明尼安德特人的丧葬活动跟象征性思维的关联。在尼安德特人的坟墓里,几乎没有陪葬物品或其他明确迹象的证据,这些似乎在早期智人身上更常见。没有明显象征意义的东西,比如鲜花或坟墓,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古人类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当然,想象尼安德特人也具有埋葬死去同伴的能力,且出于跟我们一样的理由,其实并不算太过分。他们的大脑非常大,与现代人的脑量相当。可以想象,他们拥有堪比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复杂行为。即便科学家们想要承认尼安德特人的确有资格被视为一个具备丧葬仪式的种群,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认为:惟有脑容量大到一定程度的原始人才能从事这类象征性活动。
“纳勒迪智人”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他们的大脑还不到现代人类大脑的一半。我们不妨这么来看:“纳勒迪智人”让丧葬与象征性思维之间的关系显得愈发扑朔迷离了,这些生物出于实际原因而特意处理死者的尸体,但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问题在于,为什么“纳勒迪智人”非要想方设法穿越黑暗,把自己的遗体放到洞穴深处?现在有证据支持另一种可能性,这些看似原始的生物实际上是在从事复杂的、深刻的情感行为。
通过挑战象征性行为和尸体处置的既有观点,“纳勒迪智人”迫使科学家重新考虑长期以来对这种行为的假设和想法。也许殓葬仪式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独特,并且只有人类才有。即便我们把尼安德特人和“纳勒迪智人”也放到有丧葬仪式的原始人群体中,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承认某些人类自诩独有的行为事实上也与其它种群所共享。
直到20世纪60年代,工具制造被广泛认为是只有人类才会去做的事情。然后珍·古道尔(Jane Goodall)亲眼目睹了黑猩猩修改材料来制作自己的工具的场景。作为对这一消息的回应,她的导师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ey)在电报中说:“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类,或者接受黑猩猩作为人类的观点。”
也许埋葬再次提醒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解剖学的进化过程中,这种模糊的界限现在得到了充分的承认。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明显的“人类”特征实际上是零碎出现的,且模式也不可预料。举个例子,直立姿势和大脑容量的增加似乎是断断续续出现的,而且还伴随着一些逆转。我们的祖先似乎以“马赛克”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其中包含了一些现代特征,同时也缺乏其他特征。
也许这种马赛克式的进化也适用于人类行为。难道我们的文化(包括抽象思维和复杂的象征性行动)不是一步到位突然出现的,而是逐渐演变累积的吗?这一假设引出了关于人类本性出现的新问题,并提出了寻找证据的新方向。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认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看待变化、创新的方式有了广泛的转变。他们认为,应该将人类的进化从起源和革命的特殊时刻进行概念化,而不是将人类整个进化过程概念化,这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逐渐演变上。这种思维上的转变认为,渐进式进化过程比突然创新的时刻更重要。
推动这一概念的人类学家认为,打破诸如将复杂认知和文化发展细分成不同的过程,这会为我们提供新的洞见,以更细致的方式来审视这些部分,这比试图完整地理解整套方案更有启发性。如果将埋葬过程分解为实践和认知过程,那么复杂的仪式可能更容易被理解。人类的丧葬行为与原始人乃至其它关系更为疏远的种群的丧葬行为之间的界限,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它最终可能会允许更详细的跨代比较,从而更好地了解其他物种,以及我们自己。
人们认识到,人类文化可能是逐渐出现的,过程中充满了起伏,暴露出一种常见但缺乏基础的假设。如果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人类的重大转变是同时发生的,比如我们突然进化成为现代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就掉进了这个陷阱,他假设双足行走、大脑体积增加以及解放双手来使用工具是同时发生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的出现,这幅画面变得更加复杂。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和其他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表明,这些过程发生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
如果“纳勒迪智人”真的出现了象征性行为,那将提出一个更宏大的问题:科学家是否应该全盘否定人类独特性的想法?几十年来,有些学者一直在争论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一味探寻人类独有特征的思路使我们较少关注细小的变化,并且还不愿意承认差异是个程度问题。他们还警告说,界定人类独有特征的做法其实含有一系列价值判断,如“什么东西在当下而言对我们是重要的”。
在《野兽与人》(Beast and Man,1979年)中,道德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认为:“如果有人想要搞一场谁更像人的比赛,然后自己给自己颁奖,那反对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但这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以循环论证的方式提出各种价值判断,以判断人类生活中什么东西最重要。”
理解人类进化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人类学家来说尤其重要,他们经常被指责站得离人类家族树太近,无法看到更大的图景。从这种有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将进化聚焦在智人身上,而其他生物的进化截然不同。认识到人类行为存在马赛克有可能改变这种思维定势。
通过抛开“我们的行为独一无二”这个信念,我们或许就能认识到:我们喜欢把自己看得很特殊,这种倾向实际上让我们远离了灵长类动物这个大家庭,难以充分理解它的进化历程。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2015年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纳勒迪智人的发现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反思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与自然业已破裂的关系:“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契机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承认这些区别的模糊性呢?”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自其它媒体的文章,目的在于弘扬科技创新精神,传递更多科技创新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在此我们谨向原作者和原媒体致以崇高敬意。如果您认为本站文章侵犯了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