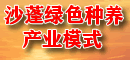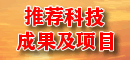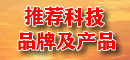2016年8月16日凌晨,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升空。从此,浩瀚的星空中多了一颗中国制造的“量子星”。
就在此前几天,另一枚“重磅炸弹”已然释放。2016年8月8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其中明确提出部署“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重大项目。
“墨子号”不仅将中国人的名字写进了量子物理学历史,亦如一颗投入水中的小石子,激起层层涟漪。美国、欧洲、日本纷纷启动国家级量子计划。
智者先行,故从者众。它们追赶的目标只有一个——中国。
搭上改革快车
“以前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来这里。”坐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办公室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研究院)院长潘建伟向《中国科学报》感慨说。
2007年,为了方便同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技物所)、中科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开展卫星量子通信的关键技术攻关,潘建伟的团队选择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作为落脚点。
时至今日,这里仍未被公共交通网络覆盖,距离最近的公交车站、地铁站都在两公里以上。那几年,团队的骨干成员每天去30公里外的上海技物所“上班”,有时加班太晚,干脆就住在附近的宾馆,第二天起来接着干。
为了“墨子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同中科院系统的多家兄弟单位——上海技物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光电所)等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样的基础使其日后顺利成为中科院首批启动建设的4个卓越创新中心之一的核心团队。
2014年,中科院启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作为提纲挈领的一项重要举措,研究所分类改革得以迅速展开。其中,集合优势单位协同创新,发挥“尖刀连”的作用,并在某一个方向迅速迈向国际前沿,是卓越创新中心承担的历史使命。彼时,中国科大的量子信息科技研究正好具备了这样的基础。
量子指的是物质不可再分的基本单元,例如光量子(即光子)就是光能量的最低单元,不可再分为“半个”光子、“三分之一”个光子了。量子纠缠是奇特的量子力学现象。通俗地说,两个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的粒子就像有“心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测量得到某一结果,另一个粒子也会瞬时相应塌缩到某一量子状态。因此,由此衍生出来的量子通信技术,是唯一被严格证明的无条件安全通信方式,可以有效保障国防、政务、金融等领域的信息安全传输。
量子信息科技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已不言而喻,世界各科技强国都投入巨资抢占制高点。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量子信息科技的实验研究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中国科大虽然起步较早、在某些方向领先,但几支团队规模都较小。
“慢慢地我们发现要做出高质量原始创新,靠这种单一实验小组的模式不行。”潘建伟回忆。尤其是2011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启动,这项原本属于基础研究的工作正式进入追求零失败的航天工程领域,愈发凸显出多学科交叉、各项关键技术集成的必要性。
中科院高度重视量子信息科技的布局和发展。2014年10月,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卓越中心)正式成立,依托中国科大建设。
成立之后,国际国内形势风起云涌,卓越中心很快产生了危机感。在国内,量子信息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层面抓紧部署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并积极筹建量子信息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国际上,第二次量子革命方兴未艾,美国、欧盟、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投入重金部署国家级量子科技计划。
“这意味着我们随时有‘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风险,本来我们只把‘脑袋’放到卓越中心,现在则需要部署全链条集成。”潘建伟说。
2016年底,卓越中心适时向中科院党组提出,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国家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的战略,将小而精的“尖刀连”拓展为体量更大的“集团军”——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这一请求迅速得到响应。2017年7月,卓越中心正式转为创新研究院,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并为筹建国家实验室作积极探索。同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联合批复,而创新研究院将作为骨干力量参与建设。
“可能因为我们的方向比较新,总是幸运地赶上中科院改革的第一班车。”潘建伟说。
搭着这班顺风车,卓越中心以及其后的创新研究院很快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学”研究成果获得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首次实现多自由度量子隐态传输,并被英国物理学会评为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之首;开通首条远距离量子通信干线——“京沪干线”,为探索量子通信干线业务运营模式进行技术验证,已在金融、电力等领域初步开展了应用示范并为量子通信的标准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实现首次洲际量子通信,构建了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雏形,并被美国物理学会评为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事件;研制出世界首台针对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
《自然》杂志评价称,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
结合“墨子号”与“京沪干线”构建的首个天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雏形中科院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供图
十年磨一剑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科大和上海技物所在“墨子号”上的合作,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碰撞”。
第一次“碰撞”发生在2009年。
外太空因为几乎真空,光信号损耗非常小。将卫星作为中继器,可以大大扩展量子通信距离,甚至实现全球化的量子通信。为验证这一大胆设想的可行性,中国科大和上海技物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单位合作,首先在青海湖进行百公里量子通信实验,量子纠缠源则设置于湖中的一座岛上。
岛上没水没电,昼夜温差大,冬天湖面结冰,只有一座寺庙和一些僧侣。为了避免日光的影响,量子实验都在晚上进行。于是,几个年轻人夏天上岛,晚上做实验,白天下山挑水,再上山洗衣做饭。帐篷、炉子、发电设备都要自己搭建。青海湖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每10天过来送给养,此时便成了科研人员最热闹的时光。
为了积累数据,实验一做就是3年。2012年8月,潘建伟等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百公里量级的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和纠缠分发,这意味着在高损耗的星地链路中,也能够实现单光子级别的量子通信。
经过这次磨合,第二次的“碰撞”更是火花四射,因为这一次,他们不仅要将实验搬出实验室,还要搬上太空。
作为世界首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度可想而知。上海技物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系统总指挥王建宇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以前做各种各样的卫星一般都有个参考,但量子卫星真的没底,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
关于星地间量子纠缠分发的难度,王建宇曾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就像在太空中往地面的一个存钱罐里扔硬币。不仅如此,天空中的“投掷者”相对地面上的“存钱罐”还在高速运动。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中国科学家不仅要做世界第一颗量子卫星,还要做一颗有实实在在科学影响力的量子卫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个团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为了实验更出色,“激进”的科学家不断提出新的想法,而“保守”的工程师则希望减少改动,提高稳定性。
“那段时间,我和王建宇也经历了激烈的磨合。事实证明,干大事必须精诚合作。”潘建伟坦言。所幸,这是一颗深深打上中科院烙印的卫星。
“科学家只要提出想法,我们就照着设计。大家都是科学院出身,骨子里追求卓越、渴望创新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上海技物所研究员、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系统副总师舒嵘说,虽然课题组间也有自然形成的合作,但和卓越中心、创新研究院体制下的合作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碰撞”的结果是,“墨子号”各项性能都优于设计指标,原本计划两年完成的科学实验任务不到一年就完成了。2017年6月,《基于卫星的纠缠分发距离超过1200公里》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在《科学》上。“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研团队也因此获得2018年度美国科学促进会克利夫兰奖,这是90余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研成果首次获得这一重要荣誉。
“这个时候我们的合作已经体现出了创新研究院的价值,那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潘建伟认为。
为了卫星上天,团队里的年轻人有的从科学家变成“半个”工程师,有的则从纯粹的工程师进入了前沿研究领域。
其中就包括科学应用系统主任设计师、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任继刚。任继刚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第一次听潘建伟作报告,仿佛在听一个科幻故事,没想到日后竟成了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春节,我们做实验做到年三十凌晨3点。”他说,直到2017年实验基本完成后,所有人才度过了一个“史上最开心”的春节。
2016年8月16日,经过中国科大、上海技物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所、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十多个团队历时5年的合作,“墨子号”成功发射。所有人长舒一口气,但这不是终点。
卫星于凌晨升空后,几位主任设计师立刻从酒泉赶往各地面站。由于卫星在夜晚经过,且在地面站上空的过境时间仅有几百秒,因此一入夜,河北兴隆、青海德令哈、乌鲁木齐南山、西藏阿里、云南丽江5个地面站便忙碌起来。
“8月18日凌晨,我们在德令哈地面站第一次将地面的信标光覆盖到‘墨子号’,为离开地面近48小时的‘墨子号’点亮了灯塔,建立了星地互联的第一步。”量子纠缠源载荷主任设计师、中国科大教授印娟回忆说。
2017年8月,“墨子号”提前一年完成星地量子纠缠分发、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三大既定科学目标,向世界宣告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尺度的量子科学实验研究。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对此评价:“墨子号”开启了全球化量子通信、空间量子物理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的大门,为中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成为国际同行的标杆,实现了向“领跑者”的转变。
回忆起这次合作,王建宇有四点体会:“第一,原创的科学思想是灵魂;第二,决策层下定决心让科学家去闯,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第三,团队协同作战效果显著;第四,科学团队和工程团队必须互补。”
最优最简互补
在人才培养上,潘建伟有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做法,那就是将优秀的学生有针对性地送到国际顶尖团队学习和开展合作,再将掌握的关键技术带回国内。
于是,陈宇翱去德国马普所、赵博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张强去斯坦福大学研究参量上转换探测器,陆朝阳去剑桥大学研究量子点光源,张军去瑞士日内瓦研究单光子探测器……
潘建伟回忆说:“当时国内实验室很缺人,但不把人送出去学习的话将来这把火肯定烧不旺。所以尽管国内对人才极度渴求,但还是把人送走了。”
如今,随着这批年轻人的集体归国,这把量子通信的火真正烧起来了,他们也个个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室负责人。
卓越中心升级为创新研究院后,改变了过去几个团队各为一个研究室、相互间仍以自发合作为主的组织模式,统筹设置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光电子与微电子器件4个研究部,每个研究部下设若干个研究室,整合相关的优势研究力量。例如,量子计算研究部包含光量子计算、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离子阱量子计算、硅基量子点量子计算等多个研究室。组成每个研究室的各个团队,围绕研究部的主任务,在各个分系统上开展协同攻关。
如何让这么多人彼此不重复又能相互促进、协同创新?“我们的原则是‘最优最简互补’。”潘建伟吐露了秘诀:“创新研究院每次引进人才时一定要问三个问题:是不是全国最好的?是不是有重复?能否形成互补?”
按照“最优最简互补”的原则,创新研究院在建设过程中重新调整了组织架构,根据我国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已有的区域集群优势,形成了“合肥总部+北京分部、上海分部、济南基地+相关研究单位”的研究队伍布局,各部分朝向一个共同的主任务,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这种科学组织架构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耗”和“打架”,也让创新研究院近年来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量子科技涉及物理学、信息学、材料学、工程技术等众多领域,一家科研机构难以包打天下。为此,创新研究院独具特色地联合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力量,形成全方位的协同合作网络,并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积极组织全国力量协同创新、集中攻关。
通过制度改革,创新研究院不断加强依托单位与共建单位的协同创新合力,并建立起大型仪器设备、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科技资源的统一管理机制,充分提高了已有资源的统筹利用效率。
“通过项目将大家组织起来,协同全国的科研力量,但又不是完成项目后一哄而散。”潘建伟表示,从前每个团队都需要进行全链条创新,现在则可以只做自己擅长的部分,推动各学科协调发展。
同地方共建也是创新研究院的一大特色。在引进人才方面,安徽省和合肥市都提供了力度较大的政策支持。不过,对于创新研究院来说,真正能留下人的还是事业。以“墨子号”团队为例,具体负责项目的主任设计师几乎全是“80后”。任继刚、印娟等人都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科研骨干。
“青海湖的项目完成后,潘老师提出让我留下继续做卫星,刚博士毕业就能做卫星吗?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任继刚回忆。
研究超导量子计算的朱晓波则是从兄弟单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加入创新研究院的。不久前,他们刚刚成功实现了12个量子比特的多体真纠缠态“簇态”的制备,刷新了超导量子比特纠缠的世界纪录。
“量子计算机意义重大,我们的目标是做出实际应用。”朱晓波说,超导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量子计算方案之一,也是谷歌、IBM等商业公司投入最大的方案。
“我们在这一方向上虽然是追赶者,但创新研究院可以凝聚力量形成协同攻关,跟世界最前沿的研究组竞争,不管中间有多困难,都不会改变我们的信念。这也是我加入创新研究院的原因。”朱晓波说。据悉,在创新研究院,朱晓波除了自己的学术团队,还有一支近30人的团队为他们提供支撑服务。
“创新研究院的作用就像土壤。”潘建伟说,“在单个研究小组中,很多种子只能长成花盆中的盆景,但在创新研究院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的模式下,我们希望每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目前,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实施方案已形成,专家组一致建议尽快启动。作为我国量子科学领域研究的领军机构,创新研究院将牵头肩负起这一重大项目,着力解决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领域一系列前沿科学问题,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和核心器件,培育形成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速加速再加速
20年前,潘建伟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量子信息科学,欧洲美国都刚刚起步,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做?每次他都耐心讲解量子科技革命的意义,结果却不尽人意。“难度太大”“不靠谱”“做不成”是他最常听到的评价。
潘建伟认为那段时间是自己研究生涯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学科方向不被理解,申请经费四处碰壁。
2002年,潘建伟提出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的构想,同样遭到了各界质疑。一筹莫展之时,他接连从中科院获得了“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在一次项目申请会上,面对诸多质疑声,当时中科院分管基础研究和人才引进的领导发言强调:潘建伟发过很多高质量文章,得到了国际认可,科学院作为支持原始创新的机构,能不能让他试一试?
就这样,潘建伟拿到了中科院的经费。他很快在2004年底进行了国内第一个自由空间实验,在合肥创造了13公里的双向量子纠缠分发世界纪录,而此前的国际纪录是600米。由于整个竖直大气层的等效厚度为10公里左右的近地面大气,实现了13公里的量子纠缠分发就意味着光子能够突破大气层,有效验证了星地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到了2009年,当潘建伟向着实现星地量子通信的梦想努力前进时,主要的质疑声依然是那个问题:卫星量子通信,外国都没人做,我们是否太冒失?那时,我国以业务卫星为主,科学卫星渠道很少。关键时刻,又是中科院前瞻性地设立了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墨子号”幸运地成为专项支持的首批科学实验卫星之一。
潘建伟没有辜负期望。“墨子号”和“京沪干线”引发的“蝴蝶效应”是巨大的——欧美国家明显加快量子通信领域的布局,同这两项工程在我国率先成功实施直接相关。
“中科院能相信我的科学判断,让我往前走一步,是需要勇气的。而我们能够20年来坚持在科学上毫不动摇,也是因为有中科院体制的支持。”潘建伟强调说。
支持越大,责任就越重。“墨子号”是一颗低轨卫星,每天经过中国上空两次。王建宇透露,在国家支持下,创新研究院计划再设计一颗高轨卫星,以便未来可以随时随地做实验。“这次的难度就不是扔硬币了,可能比纽扣还要小,但我们已经在准备了。”
印娟则介绍,创新研究院正在着手制定相关模式标准并推广到全球,等未来建起一张全球量子卫星通信网时,我国将发挥主导作用。
2017年11月,美国开始禁运量子密码相关设备和器件,12月又扩展到包括整个量子信息和传感等14个领域。随后,欧洲也陆续开始禁运相关设备。
“以前我们能在全世界购买性能好的元器件,后来他们不卖了,我们只好买材料加工。好不容易加工品质提上来了,高品质的原材料又不卖了。现在更糟糕,凡是跟量子信息加工有关的产品都不卖了。”潘建伟说。
做分子束外延的中国科大教授霍永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引进的。他坦言:“如果在10年前未必会引进我,但现在不同往日,我们只能自己做。”
近几个月,潘建伟感到自己的思想转变很大。“以前是集成全球的创新要素做创新,现在就必须考虑,如果别人什么都不给,我们还能不能创新?!”
在他看来,这更说明从卓越中心转到创新研究院的必要性。量子信息科学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创新研究院的目标亦不仅仅是发表文章,完成转化应用才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的价值。“再不加速就真的只能停留在基础研究了”。
目前,量子通信是创新研究院四大方向中最接近于实际应用的方向。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全长2000余公里,目前正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制定标准,为将来量子通信干线的商业运营和规模化应用奠定基础。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的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量子传感等方面,创新研究院也将为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创新研究院一定要领跑,不然就变成了‘跟踪研究院’。现在国际上追赶的速度很快,很多方面我们还要向别人学习,丝毫不敢懈怠。”对于未来,潘建伟如是说。(记者 陈欢欢)